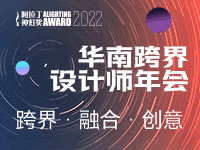建筑师简介:
王灏,润·建筑工作室(Rùn Atelier)联合创始人,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客座导师,同济大学建筑系本科毕业后留学德国斯图加特大学,回国后将主要精力投入在民宅的设计上,做了很多自宅、民宅的项目,在网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其设计的春晓自宅于2013年获得了德国《世界建筑》杂志全球处女作奖住宅类最高奖项。
目前做过的(包括在建的)项目包括:
2007-2009年 库宅(宁波)
2010-2013年 王宅(宁波)
2011-2013年 柯宅(宁波)
2012-2013年 胡宅(宁波)
2013-2015年 五号宅(宁波)
2010-2014年 柯力博物馆(宁波)
2014-2016年 柯宅二
2015-2016年 胡宅(杭州)
2015-2016年 汪宅(苏州)
2015-2016年 叶宅(佛山)
导语:
这位意欲在中国民居领域深耕细作的建筑师,深信民居是建筑设计遗漏的处女之地,在这片处女之地上,民宅的设计拥有着广泛的探索性、自由度,任由建筑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耕耘民宅这块处女地,建筑师往往需要更综合的素质,建筑师更像一个“总控”,一人兼具了室内设计师、家具设计师、灯具设计师甚至是灯光设计师的职能。而在王灏看来,灯是住宅的精灵,很多时候空间氛围的塑造是靠灯的,在哪个位置,用什么造型,用多少灯具,高度多少,营造出什么样的氛围,对居于其中的人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阿拉丁·设计》:目前润建筑或者说您做过的作品大多数都是民宅,当初选择做民宅而不是像大多数建筑师一样将精力放在一些庞大的项目,是偶然还是有意为之?
王灏:当初也没有想得这么清楚,只是有些朋友或者亲戚要盖房子就找到我,于是做了一些民宅的项目。倒不是要把自己归入商业建筑师还是民宅建筑师,只不过在做民宅的过程中,自由度、专业范围的探索性都没有什么束缚,你可以充分地去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没有一些不必要的干扰。一个大房子或者一个博物馆,往往会有开发商或者主管单位、投资方或者未来的使用方等等从各自角度出发的观点,都会使这个房子丧失一些形而上的东西,比如哲学性、审美立场等,这些东西是非常纯粹的,一旦有各种社会需求的牵绊的话,就会使这个房子丧失它原有的纯粹性和自由度。
另外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我们认为中国的建筑首先是从解决住的问题开始的。所有传统的建筑,广东的民居也好,浙江的民居也好,都是艺术性跟生活性结合得很深的成果,这个成果非常有意思,但长期被主流的建筑界所忽略。因为我们的研究往往停留在如何保护古建,而不是如何去延续传统的精髓,做一些新的尝试(新的民居),使其具有传统的精气神,同时又符合现代人的生活方式。这里面涉及到国家土地政策的问题,涉及到市场收费的问题,这导致很多建筑师有心无力。另外,这个群体可能有比较偏激的想法,很难跟现代的一些设计理念对接(沟通)。这方方面面的原因就阻止了很多力量进入我们国家最有创造力的一个领域,因此在这个领域的探索才显得弥足珍贵。
《阿拉丁·设计》:民宅的项目更关注“生活性”“实用性”, 外观往往会被忽视,您如何理解建筑的外观和功能性之间的关系?
王灏:通常,我们对待一个好的东西有两种态度:一是藏起来,比如说我们的传统园林,都是藏起来的,一个围墙一个大门围起来,外面露出一些树、亭台楼阁的一个角,你是看不到它的全貌的,它都是封闭的。古代传统文化都是以“藏”、“内敛”为特色;另一个,我们评价一个好的地方,就说它“藏风纳水”。而露出来是西方的一种文化态度,它重视的是怎么样去推广、怎么样去传播,所以你看到法式园林从来不会有围墙。西方的宫殿建筑也好,民宅也好,也是以露为主。
回到中国民居的外观,我觉得这是一个哲学立场的问题。如果你要接纳传统的哲学立场,你的(民居的)外观要做得很朴素、低调、不显眼;如果你要接纳西方的哲学理念,就意味着你要露出来,你要有漂亮的立面、漂亮的入口,要有个性。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代世界,所以很多时候这两者是并存的。比如说面对一个文人的时候,他希望是藏起来;面对一个商业建筑的开发商的时候,他可能希望露出来,因为他要去招徕客户。所以,我们现在大部分的建筑是以露为主的,背后表达的是一种开放性、商业性、现代性。
[NT:PAGE] 其实,这两者也不是完全矛盾的,这取决于这个建筑是用来干嘛的。如果是民居就没有露的需要,我的生活方式不需要露给别人看。当然也有些人特别开放,有这方面的需求,根据需求的不同,处理的方式也不一样。我们做过的大部分民居看上去都蛮低调的,目的就在这里。居民的生活方式是藏起来的,就意味着外表有可能很简单,甚至很丑陋。如果,你要阅读这个房子就一定要进入这个房子的内部,才能了解它。
当然,那种想露但是露得还不够好的房子在中国非常多,有可能是因为业主的美学水准在这里,或者建筑师的美学水准在这里。
《阿拉丁·设计》:说到这里我就想起来之前我们采访的一位建筑师,他认为建筑的功能的改变会对人的生活方式产生影响和改变。您怎么看待建筑的功能性对生活方式的改变?
王灏:我们认为一个民居它代表的是当代或者古代的一种生活方式。古代的社会伦理或者社会道德会对个人的要求会非常高,比如小孩要住哪儿,老人要住哪儿,有这种规矩,现在这种规矩非常少了。我们设计的民居,希望培养一种新的道德和秩序,一种有节制的生活、绿色的生活,不要铺张浪费,还要有规矩。比如说你的卧室不要太大,你的客厅也不要太大,可能里面还要有天井,天井是对传统的一种延续,通过这个天井你可以回想起古代,回想起传统要求的一些事情。这种东西是肯定会影响到个人的。一个好的民居本身肯定会有一些高于功能本身的空间设置。这种空间设置你可以说它是一种延续,也可以说它是一种教化,也可以说它是一种暗示。总的来讲,总是希望居住在这个空间里面的主人产生一些跟住在商品房里面不一样的变化。这种变化是非常重要的,就跟你出生在书香门第,你身上也带着一股书香气息是一样的。
《阿拉丁·设计》:经过这些年来的探索,您认为民宅该如何去处理跟周围环境、肌理和人文的关系?
王灏:我们有几个原则,一个就是刚才已经谈到的“藏起来”的原则,外表是一种封闭、接纳的姿态,比如说我们一个村庄,基本上都是熟人,倒推一百年可能大家都是亲戚关系,意味着大家做的房子都会有一种相似性,外表看上去差不多的,所以我们要把最重要的东西表现在内部空间,而不是房子的外表。
第二个原则,因为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独特的气候或者建材,我们会去尊重当地的气候性或者建材。一方面是降低这个房子的造价,另一方面也是增加这个房子的社会性。而真正影响房子核心思想的是设计哲学,设计哲学是非常形而上的东西,指导着我们怎么去布置空间,怎么去利用结构,然后落实到当地的建材、造型,是可以根据地域的变化而做出调整的。这样每一个房子看起来都很好地融入了当地的氛围。
《阿拉丁·设计》:不管是民宅还是其他的项目,通风、采光通常都建筑师非常关注的两个因素。您如何理解建筑和光的关系?
王灏:光有两种,一种是自然光,一种是人工光。国内很多房子的自然采光做得很差,大多数都是靠人工光来解决照明问题。很少有房子可以通过自然采光来满足室内的照明,都需要靠人工光。我认为一个好的房子一定是人工光环境跟自然光环境有着很好的契合。一个要降低能耗,第二是增加空间的动人性。因为只靠人工光是不会产生一种精神力量,我们很难对着一个电灯泡发呆,但是我们对着太阳时会觉得它非常伟大。
一个好空间设计,一定是光环境做得非常好的,尤其是住宅空间,对光的要求更加严格。为什么呢?因为住宅空间需要一个温馨的光环境,对自然光环境的需求更大。好的设计要考虑到这两个光环境的协调,或者互相利用。这两个光环境都是非常重要的,缺一不可。
通风也是一个大问题,古代的房子有非常好的通风,现在的房子都不考虑自然通风的重要性,就是考虑也是其次。我个人觉得这里面涉及到健康的问题,有自然通风、自然采光,人住在里面肯定会更加卫生、更加健康。
《阿拉丁·设计》:在您的项目当中,您会如何设计“光线”?
王灏:一般我们通过一些天井来采光,弥补室内光的不足;另一方面,我们会用一些粗檐、墙体来精确控制自然光对内部光线的影响。任何条件下,自然光都要比人工光好,但我们不能靠自然光解决所有的问题。剩下的就是人工光的柔和度、协调性,这就要选择不同的灯具、不同的灯光设计方式。
《阿拉丁·设计》:在民宅项目中,灯光是如何处理的?
王灏:我们会找一些专业灯光设计师做一些咨询,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氛围,是泛光照明还是重点照明,我们需要怎么样的灯具造型等等。有时候我们会自己设计一些灯具造型,因为要跟空间匹配。我们认为,灯是一个住宅的精灵,很多时候氛围的塑造是靠灯的,在哪个位置,用什么造型的灯具,数量多少、高度多少,营造出什么样的氛围,对居于其中的人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阿拉丁·设计》:您认为,建筑师和照明设计师之间如何合作会更好?
王灏:首先是前期介入,共同确定了原则之后,后期的工作就交给专业的灯光设计师负责。最重要的一点是建筑师要负责灯的造型。灯光设计师很多时候关心的是灯光的氛围,还有照度是多少?光给你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冷光还是暖光?高色温还是低色温?他关心的是灯光的质量,但我们建筑师还是要关心灯的造型。
《阿拉丁·设计》:其实做一个民宅的设计,您的身份并不仅仅是建筑师,同时还可能是室内设计师、家具设计师、灯光设计师,与普通的建筑师相比,您认为这其中的区别在哪里?
王灏:我觉得现代社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建筑师已经变成了一个环节动物了,比如说有甲方,有各种细分的分工,如果每个人掌握的专业知识都非常局限的话,是非常不利于建造一个优秀的建筑。一个好的东西肯定是天衣无缝的,美学要高度一致,各方面都要比较均衡,比如说结构、材料、人工环境、灯光等方面都有自己独到的理解。如果一个项目很大,或者切得很碎,意味着建筑师掌控能力有限,这就会导致这个项目的艺术感或者总体的高度也有限。
但在一个住宅项目里面,建筑师往往就变成了一个“总控”,控制建筑设计、室内设计、家具设计,灯光设计甚至灯具设计,最终各方面的协调度非常高,美学价值特别大,做得好的话,甚至会变成一个遗世之作。这对建筑师的综合素质要求特别高,因为你不了解室内设计、你不了解家具、不了解灯光你都很难做得好。为什么培养一个建筑师是一个艰难或者很漫长的过程呢?因为你要在了解很多知识的前提下,才能产生属于自己的观点或理念,然后去解决建筑上涵盖的所有问题。
《阿拉丁·设计》:您之前留学德国的经历,对您作为建筑师的成长影响大吗?
王灏:我觉得这段经历让我看清楚了西方的建筑,看清楚了它的优点,也看清楚了它的缺点;也看到了中国的设计哲学,中国传统的设计方式,中国古代的建筑非常伟大的地方。中国的古代建筑非常综合地解决了人与自然、人与材料、人与社会、人与伦理之间的关系,又能保持一个非常舒适的居住空间,它又是可持续的、环保的,矗立两三百年都没有问题。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说中国古建筑是不行的,也不是怎么仿古去做到古代建筑的模样。因为仿古,你是永远做不到古人的高度的,所以我们要去分析它,挖掘它,把它们一些好的东西通过一种现代的材料把它塑造出来。
通过国外的游学,再加上这几年的建筑实践,随着时间的积累,我慢慢地发现一个民居的重要性远远大于一个博物馆,也远远大于一个宫殿,因为这跟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一个博物馆做得再好,你一个月去一次就不得了了。但一个房子好,它就会培养你的生活方式,提高你的生活质量,无形中在精神方面给你施以影响,包括规矩、伦理。我觉得人是避不开这些东西的,因为空间是伦理的一个物化。
《阿拉丁·设计》:其实您留学的这段经历促使您去思考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
王灏:对的。你去看西方的建筑都是产品主义的,它们鼓励你去消费,鼓励人跟自然隔绝,房子是房子,自然是自然,一旦介入自然环境也是非常机械的介入,不像中国人这么主动地介入,它是以高能耗为代价的,这意味着它是不可持续的。
《阿拉丁·设计》:作为一个建筑师,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可能是如何不去重复自己。做了这么多的民宅项目,您是如何避免重复自己的?
王灏:这个问题很尖锐啊!我相信在50岁之前我都会自己革命,重复只说你老了或者说不要再做了,因为一旦重复了你就没有任何意义了,说明你的使命已经完成了。50岁之后,去做一些重复的事情也没有必要。你可以把机会留给年轻人了,让他们再去开拓,让他们去创新,因为每一代都有每一代的使命。